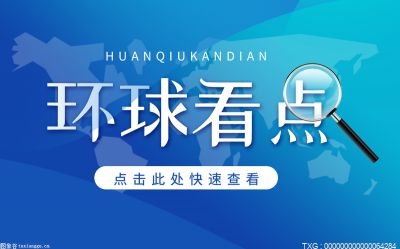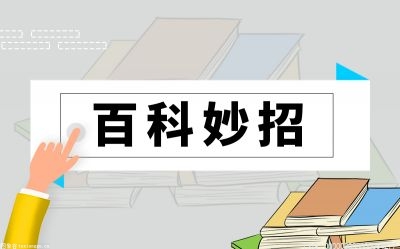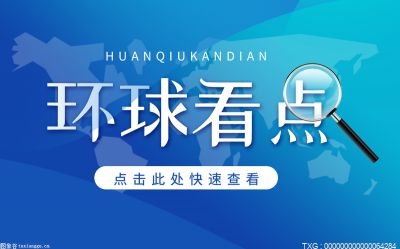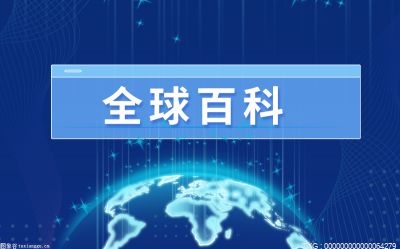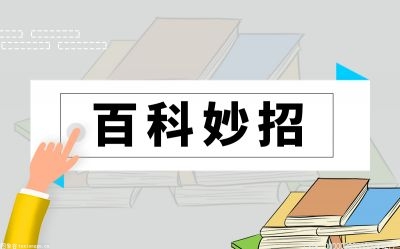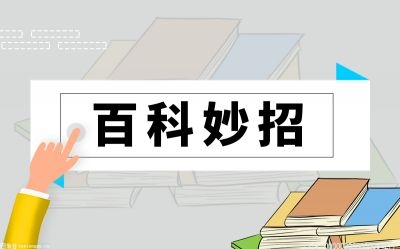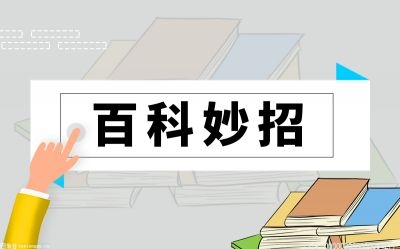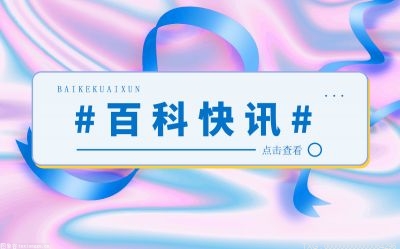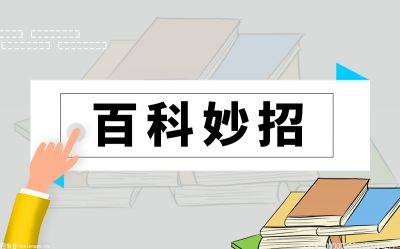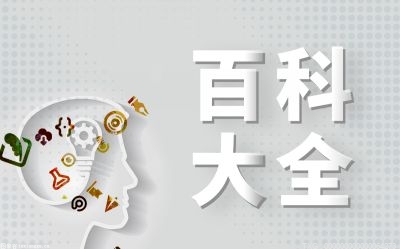白族是如何形成的?
白族属于氐羌系统的一支,其族源是多元的。白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世代居住于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――洱海人和昆明人。司马迁《史记•西南夷列传》载:“其外西自同师(今保山)以东,北至叶榆,名为嶲、昆明,皆编发,随畜迁徙,毋常处,毋君长,地方可数千里。……皆氐类也。”嶲即嶲唐,楪榆即叶榆,即洱海地区,可知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是昆明人,处于尚未定居的游牧社会。白族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属于先秦时期氐羌系统南下族群中的一支,其远祖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僰人。公元前3世纪,僰人之名始见诸记载,秦相吕不韦主编的《吕氏春秋•恃君览》说:“氐羌、呼唐,离水之西;僰人、野人,篇笮之川;舟人送龙,突人之乡,多无君。”秦汉以前僰人的分布地区,北有僰侯国,南有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数十小国,包括了北边的僰道县(今四川宜宾)和南边的滇国(今滇池周围)等广大区域。滇国的主体族是僰人,亦称为“滇僰”。汉晋时期,滇池地区仍为僰人所居,并逐渐向洱海地区迁徙。而蜀中迭经战乱,蜀人(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)四散,引起了民族的迁徙。其融合到滇池地区即滇僰的称“叟”,叟人逐渐占据了原来僰人的分布区域。东汉末年,其他部族逐渐迁入洱海地区。晋代洱海区域出现了“上方夷”和“下方夷”,洱海区域居民成分及分布有了很大变化。“上方夷”是居住在洱海北部的昆明人,“下方夷”是居住在洱海南部的哀牢、僰人、汉姓等。唐代初期出现了乌蛮、白蛮,它包括了洱海区域哀牢、昆明、西洱河蛮(又称河蛮)、云南蛮、僰人等众多部族。汉唐间,大姓爨氏兴起于南中,爨氏又分为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两部分,南诏阁罗凤时期,徙二十余万户西爨白蛮于洱海地区;在明代碑刻中仍可见到,寸、王、赵、杨四姓都认为在南诏以前他们的原籍在滇池地区,原籍“西爨故地”。由此可见,洱海地区的白族人民与西爨白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。到公元8世纪,南诏统一洱海区域进而建立起包有云南全部的强大政权,加速了白族共同体的形成。唐僖宗乾符四年(877年),南诏酋龙卒,子法(隆舜)立,自号“大封人”。“大封人”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,标志着白族的形成。从以上可以看到,从秦汉洱海人(西洱河蛮)、昆明人——东汉僰人——晋代上方夷、下方夷——唐代白蛮、封人、白人——白族,白族的族源是多元的,主要是以土著居民洱海人(西洱河蛮)、昆明人为主体,融合了僰人、哀牢人、西爨白蛮等成分,甚至融合了一部分汉族,最终于公元8世纪形成为白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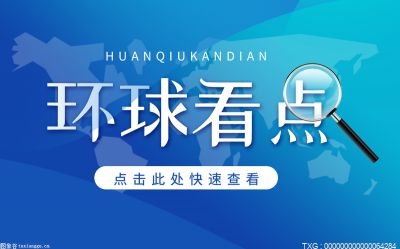
白族人的建筑有哪些风格?
白族的建筑艺术独具一格。高寒山区多居住单间或两间相连的“垛木房”或“竹篱笆房”;坝区则多住土木结构的瓦房。位于苍山脚下、洱海之滨的大理喜洲,是白族民居的精萃所在。一座端庄的白族民居主要由院墙、大门、照壁、正房、左右耳房组成。一般的建筑形式是“两房一耳”,“三坊一照壁”,少数富户住“四合五天井”,还有两院相连的“六合同春”,楼上楼下由走廊全部贯通的“走马转角楼”等,现在多是一家一户自成院落的二层楼房。充分利用当地盛产的鹅卵石来砌墙,也是白族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。白族民居往往注重门楼、照壁建筑和门窗雕刻以及正墙的彩绘装饰,门楼是整个建筑的精华部分。门楼建筑艺术水平的高低,可以反映其主人的经济地位,也是一种光宗耀祖的标志。白族门楼的挑梁斗拱不仅凸现了白族建筑艺术的精华,而且深具文化内涵。门楼正中嵌挂匾额,匾额上往往书有用来表示姓氏、发扬祖风的堂号,通常选用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或典故,镌刻在匾上。如张姓“百忍堂”、“百忍遗风”;杨姓“四知堂”、“清白传家”;董姓“三策堂”等,各姓匾额不容相混。门窗木雕,无处不闪现着剑川木匠高超的手艺。照壁是白族民居不可缺少的部分,正面书写“紫气东来”、“福星高照”、“虎卧雄岗”、“福”、“寿”等吉祥文字。